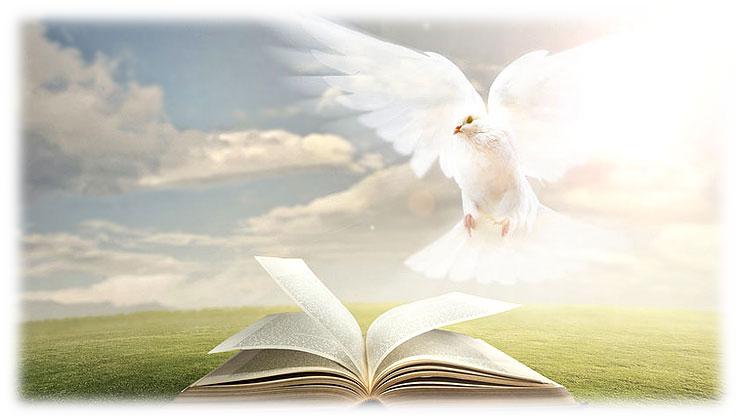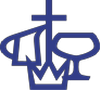|
譚景平傳道
記某日兩夫婦的對話: 到早餐店吃早餐,餐廳老闆問太太:「阿妹吃甚麼?」結果太太這個早餐吃得很愉快。餐後先生嘀咕:「為甚麼只有你被稱呼阿妹,沒有人稱呼我阿弟(音:DEE) 呢?」畢竟兩夫婦都已不年輕,若被人稱呼「阿妹」、「阿弟」,肯定是開心的。太太續說:「你若能被稱呼作阿哥就已很好了!被人叫阿弟的,只會是廿多歲的年青人,這個稱呼對你絕不合適!」先生心感不快,口中繼續嘀咕。夫婦的對話完畢。 事實上,無論任何年紀,只要聽到別人以較年輕的稱謂稱呼自己,無疑是令人感到愜意的。任何場合,被人稱呼「阿姐」總比稱呼「阿嬸」好;被稱呼「阿嬸」總比稱呼「阿婆」好。這只是一個泛現象,並非只是女性才會有這樣的感覺。 筆者不禁思想,為甚麼人對「稱呼」這麼在意,年青人想得到別人尊重,希望被看作成熟,於是介意被人稱呼「阿弟」、「阿妹」;成年人卻擔心年事已高,會被認為落伍,跟不上時代,因此常想辦法追逐潮流。筆者看來,無論哪種心態,都是因為兩者都對自己認識不深。其實年青有年青的好,成熟也必有優勝的地方。 事實上,「認識自己」是神要我們學習的功課,詩篇139是一首關於「認識」的詩篇。 「耶和華啊,你已經鑒察我,認識我。我坐下,我起來,你都曉得;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。我行路,我躺臥,你都細察;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華啊,我舌頭上的話,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。」(詩139:1-4) 原來無論意念、行動、思想、說話......各方面,上帝都比任何一個人更認識我們,甚至比我們自己更認識自己。 我們常埋怨沒有人知道自己的想法,沒有人明白自己的心思。 坊間熱門的「發現自己」課程、心靈工作坊、性向測試等,某程度上只呈現個人的片面,並不能呈現我們全面的狀況,當我們發現生命中不明顯的「惡」、「限制」、「軟弱」......時,自己會感到驚訝,甚至會選擇逃避。 「我往哪裡去躲避你的靈?我往哪裡逃、躲避你的面?」(詩139:7) 告訴我們,即使我們極力逃避,上帝的靈卻是無處不在,無處可避。同時說出一個事實:解鈴還須繫鈴人!必須面對自己才是法子。 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;我在母腹中,你已覆庇我。我要稱謝你,因我受造奇妙可畏;你的作為奇妙,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」(詩139:13-14),上帝對我們的認識,又何只是性情、思緒呢?我們是上帝所造,我們的一切,有哪些不是來自那創造者呢?上帝於我們而言,不但是創造者與受造物的關係,甚至我們的一切心思意念,祂都清楚明瞭,並且願意體恤、包容。 「神啊,求你鑒察我,知道我的心思,試煉我,知道我的意念,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,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。」(詩139:23-24) 既然如此,我們就求上帝包容到底,一直引導我們走那永生的道路。 容顏會因年日過去衰殘,頭腦也會因衰老而遲鈍,唯有在上帝的恩典中,我們永遠都有美顏、活力和智慧。 譚景平傳道
最近再次感染新冠病毒。說「再次」,也就是不是第一次了。感恩今次比起上一次的症狀較為輕微,稍為休息及服食西藥就痊癒了大半,餘下的就靠中藥調理。想來,新近感染的病況和重感冒大概差不多,當然,流感的病徴好像較新冠嚴重得多,所以大家都要保重筆者不是要發表甚麼醫學報告,實際上,一般人都認同,病後身體需要一段時間才會恢復。這個「世紀疫症」其中一個後遺症是「腦霧」,也就是指康復後腦筋沒以前那麼靈活,甚至出現「健忘症」,即俗語說的「無記性」。 健忘,通常指的是平常記得的東西,現在卻記不起來。讀者可能會說:「年紀大了,愈來愈記不起事情屬正常。」筆者也曾擔心,會不會病了一次又一次,自己會愈來愈「無記性」呢? 然而有一件事情,當與弟兄姊妹談起,發現事實並不是這樣! 當我們在正常老化過程中,腦袋的神經元並沒有減少很多,但神經間的溝通卻變差了,反應的時間變長,例如突然忘記某件事、忘記要做什麼、想不起某人的名字,但事後會再想起來,這就是所謂的健忘或記憶力退化。當然,健忘亦可能是某些疾病的徵兆,筆者亦不便評論太多,只是在「邁向健忘」時,要思想一個問題:甚麼是「健忘」?甚麼是「善忘」? 「健忘」的討論暫且擱下,因為涉及醫學上的討論。反而筆者認為,「善忘」是普遍的現象,甚至發展成屬靈上的病。 曾幾何時,學生努力背誦,到考試時頭腦一片空白,事後卻又記起,我們不會認為他是「健忘」或是「善忘」,至少他在之前曾努力記下考試內容,記不起或許是因為「緊張」的緣故。今天許多基督徒每星期都上教會聚會,可是一離開教會,彷彿如夢初醒,談到剛才崇拜的內容,講道的教導等,卻一一答不上來。當天的講道內容令人鼓舞嗎?叫人得安慰嗎?是忠言的提醒嗎?還是其他?怎麼崇拜後竟毫無印象,是需要時間沉澱思考嗎? 從前大家拿著實體聖經和程序表時,會將聽道的心得、叫人反省的字句一一記下,然後在回家路上再三回味。如今在現代科技幫助下,手機的「備忘」功能讓我們省卻書寫的煩惱,可是卻叫我們愈來愈少將聖靈的提醒記下,我們記得的可能是聽道期間,社交平台傳來的訊息。現代社會節奏急速,對許多弟兄姊妹來說,極有可能「秒秒鐘幾十萬上落」!但我們是否應時刻謹記,每個主日的崇拜是我們與主相會的時間呢?「善忘」,並不是因為我們真的忘記,而是我們沒有將與主相會的時間看重。 筆者翻查聖經,發現一個有趣的地方:「看重」在新約大多指的是人看重物質和外在的需要(林前四6,雅二3),然而舊約提到的「看重」,更多時候是指「看重」上帝的事(伯二十三12,詩一一九6,15)。 你是「健忘」和「善忘」嗎?你「看重」的是甚麼? 譚景平傳道
月初的外國足球隊訪港,引起了軒然大波,就連外國傳媒也來報道。不少球迷衝著「球王」不落場比賽,甚麼「美欺」、「未SEE」的嘲諷,甚至激進的踢破球隊的人形紙牌、衝入球場及球隊下榻的酒店等,統統做齊。政府及輿論一面倒的表示「極度失望」...... 讀者們,你是看著牧者之言,不是時事評論,筆者也無意回應這些新聞,只是在耳聞目睹當中,觸發出一點點思考。 購票入場的觀眾,當然想看到心儀的球員在場上的英姿,那怕是幾分鐘的事情。無論戰果如何,氣氛搭夠就可以了。同時期還有經典的少女組合演唱會,不少入場的粉絲都年屆中年,入場除了等待女子組合成名動作「側手翻」外,就是全場大合場熟悉的歌曲,儘管這些流行曲早已列入「經典」,甚至下架了,但氣氛搭夠最要緊;此外還有十二人組合的演唱會,不少觀眾為了得到「M」字燈牌,多昂貴的門票都願意付;因為各有所好,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支持者,只要一同喜歡這個組合,就是平日沒太熟悉的朋友都可一同觀看,無怪乎氣氛足夠就可以了...... 「氣氛足夠」是大部分人願意付出的原因,例如裝修不俗的餐廳,即使食物一般,氣氛足以滿足到自己就成了;同樣,演唱組合縱然多年來唱功沒有改善,球賽結果如何並不重要,雙方球員如何拼搏也不重要,只要球王在自己面前走動一下,滿足到自己也就可以了。「滿足」,才是人類最需要的得著。 這種「自我滿足」極其量只是一時的填補心靈的空間,時間過了,又要再找另外物事來填補了,無怪乎「娛樂事業」長久不衰。只是這種「自我滿足」的不滿足,成為人生存的「信仰」,長此下去,沒有成為心靈的雞湯,倒反了成為心靈的「鴉片」。缺乏「滿足」的人生,就像某官員道:「見到人家在踢球,我會不開心。」人家是為了你才踢球嗎?你的滿足原來建基在這些東西嗎? 原來信徒也有這種「氣氛足夠」的不滿足。敬拜的歌曲太傳統或太新,自己投入不到,沒能滿足到自己,於是離開去找別家;講員說的話不夠動聽,乾脆看網崇算了;堂會攪的活動沒新意,內容沒看頭,找過另外更有趣的參加更好,無謂浪費時間......。站在堂會角度看,筆者絕對認同活動內容吸引會眾的重要,但問題卻不是堂會的活動是否吸引,收費是否便宜,而是希望藉著參加這些活動,讓會眾經歷上帝為我們所預備的「筵席」。 正值新春,不少家庭難得聚首,吃團年飯、開年飯,有誰會責怪躲在熱廚房中,忙得天昏地暗,弄來傳統菜式、家常老火湯,手工製甜點的老媽或老爸呢?有誰會嫌棄這些毫無新意菜式呢?相信闔家團聚的氣氛、親情的珍貴,已足以滿足大家,凌駕一切! 「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在一起,要向他們行善,隨時都可以,但是你們不常有我。」(可十四7)耶穌的門徒即使長年與耶穌一起,卻沒有在耶穌身上得到滿足,甚至以為一個常顯神跡的夫子才是真正的神。耶穌斥責他們,沒有以基督的信仰成為自己的滿足,甚至「與耶穌一起,卻沒有耶穌」,這不也是同一種的悲哀嗎? 讓我們珍惜身邊同樣珍惜你的同路人,不要只為自己滿足,而輕視別人在你生命中的價值,否則如何隆重的氣氛,也不能滿足自己。 譚景平傳道
身邊總有一兩個新手爸媽,筆者家中弟弟和弟婦正是!他們其中一個話題,就是小朋友到了兩歲左右,忽然就好像出現一種懂得選擇的意識。然而小朋友的選擇,卻是不斷的說「不」,所以很多新手爸媽都稱這階段為「trouble two」,視為夢魘!後來還有隨之而來的「XXX three/four」(讀者自行植入吧,想也不是甚麼令人睡得好的字眼!) 玩笑開過了,筆者思想到,為甚麼會有這種選擇?誰教小朋友在選擇時以「不」來回應呢?某程度上,這種「選擇意識」在孩子成長時想必會製造了不少痛苦,甚至破壞。 隨著人不斷成長時,選擇往往愈來愈多,由不吃某些食物,慢慢變成「挑食」的惡習,到選擇乘搭交通工具 (某次筆者侄兒堅持在深夜選擇乘長途巴士回市區,最後苦了翌日返早班的父母),以至長大後選擇朋輩相處,人原來都會以「不」來表示個人的喜惡!「我唔鐘意同佢玩」、「我唔要佢同我一齊」、「我唔鍾意同佢一組」...... 這些說話中存在很多的「不」,也存在多少人的自我中心! 教會是一個「共融」的群體,對某些人而言,這是「金科玉律」,然而實行時卻「講一套做一套」,說甚麼理據,說甚麼制度,倒頭來是自我中心的演譯:只要我喜歡!所謂「共融」,只是電影院的「不日上映」! 上帝也很奇妙,創造伊甸園時就讓人有「自由意志」,「耶和華神吩咐他說:『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,你可以隨意吃,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,你不可吃,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!』」(創二16-17)讀者可能會說:「就是啦!若不是讓人選擇,始祖就不會墮落吧!都是神的不好!」筆者大膽假設,上帝沒有創造分別善惡樹,那麼人就不會墮落嗎?那叫上帝不要創造這、不要創造那,甚至不要創造令我討厭的他/她,豈不是很好嗎?若然這樣,你豈不是操控了上帝?更惱恨了上帝的創造!(筆者寫到這處,也感到汗毛直豎!!) 原來人的選擇,背後來自太多自我中心! 那麼讀者又可能會說:沒有自我中心豈不更好?筆者並不建議鐘擺到另一邊,而是我們當知道選擇是上帝的恩賜,祂讓我們選擇,也要我們明白「挑」會挑對,也會挑錯,既是一種選擇,也是一種學習。誰說做錯了選擇會回不了頭?約瑟的十個兄弟如是,浪子如是,彼得如是。我們也是一樣!選擇是一種成長的學習,讓每個人在選擇中,了解上帝創造的奇妙。 畫家嚴以敬(阿虫)其中一幅作品:「甜的吃,苦的也吃」,畫的是苦瓜。有些人到老也不吃苦瓜,失去親嘗苦瓜滋味的機會。我們會有選擇的時候,選對選錯,也是進一步的認識自己,進一步了解上帝的創造! 譚景平傳道
2023年將近告終,各界都對本年一些觸目的人和事作出總結。時代雜誌也選出本年的「風雲人物」(Person of the Year)。本年度的風雲人物由泰勒絲(Taylor Swift)獲選,讀者或許對這位藝人認識不多,但她卻是筆者其中一位欣賞的人。筆者認為若說她是藝人,似乎忽略了她的其他成就。 這位33歲的女士,出道已有16年(17歲已經發表作品),《love story》成為她其中一首著名樂曲。她這次獲選為年度風雲人物,是九十六年來首位單獨獲選的藝人;她的的對手殊不簡單,包括每位女孩夢寐以求的「芭比娃娃」,甚至新任英國君主查理斯三世,也敵不過這位小妮子,可想而知,這位女子是如何厲害! 泰勒絲厲害之處,在於她的作品雖然充滿鄉村風味,卻能以簡單的旋律、貼近生活的歌詞,牽起聽眾心底的悸動,她創作的輕快的流行曲調常成為人快樂的來源,讓人翩翩起舞。泰勒絲的音樂天賦在她的作品中表露無遺,甚至引發起人們研究她的作品中的歌詞背後存在的教育及文化意義,美國甚至有幾所大學開設「泰勒絲研究」,去探究泰勒絲的影響力如何擴展成一種文化現象。 我們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!一個年青小女孩竟可以引發出一種文化現象,影響到現實世界中的人!但原來我們卻早已認識一位,比泰勒絲厲害很多倍的人物。這個人用自己33年的人生,去闡述一個關乎每個人生命的信息,又行使出一個個叫人意想不到、令人驚訝的作為。祂所做的平凡卻獨特,但不被這世界接受,接受祂的人一般只是凡夫俗子,君王領袖卻對祂所作的視而不見,甚至為了祂對世界的影響竟想把祂置之死地。祂的作為扭轉了世界,祂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,世間如何高等的學府,智慧怎樣過人的學者,都想不出所以然來,只能說是「恩典」。 「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,為你們生了救主,就是主基督。」(路二11) 這位我們早已認識的人物,「許多人因祂驚奇;祂的面貌比別人憔悴;祂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」(賽五十二14) 但是卻帶來驚天動地的改變。 今天就是了!你準備迎接祂了嗎? |
牧者之言每星期一篇, 發佈日期
四月 2024
牧者
全部
|